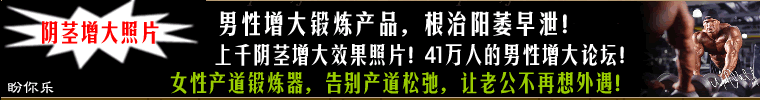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我班里流传一种名叫《少女之心》的手抄本,不太准确地说,是在男生中间流传,女生有没有看我不知道。那一阵子,不少同学都在早自习课上埋头苦读,有的埋头苦抄,学生们的专注精神让老师大为惊讶,终于,有个姓马的哥们老师逮住了。老师没有声张,只是抓过手抄本撕得粉碎,然后把那位姓马的男生扭到教室外面狂扇耳光,把小马的脸扇得像猴屁股一样红,吓得我也没胆量去借《少女之心》看了。有一点我必须说明──我想看,而且想看得要命,尽管当时才十岁,这不仅仅是好奇的问题,那位撕掉《少女之心》的老师被我们骂了好几年。
中学时我看到一本书,里面有篇东西名叫《远征瑞典》,作者署名为司马淫,说的是一个香港青年到瑞典去做爱的故事,为什么去瑞典呢?因为那里的人从小就进行性教育,风气相当开放,做那种事和吃饭没什么两样。文中的香港青年在瑞典大开洋荤,我们在宿舍里读得热血沸腾,读完之后急得活蹦乱跳,我恨不得长身翅膀,飞到遥远的瑞典,真后悔当年没去北欧投胎。
我们在校园里所受的教育里很纯洁的,纯洁得几乎就是为了考试。初中时我们开了生理卫生课,尽管老师有意跳过某一章,并声明那一章在考试中并不占多少成分,但我还是把那一章看得滚瓜烂熟──考上大学后,全国各地的青年聚到了一起,彼此一交流,噢,原来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考高中时分数正好上线,生理卫生课得了满分,功不可没,我得感谢某一章节,完全是因为它我才对《生理卫生》兴致盎然。
应试教育体制中性教育的缺失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好处,他们主要是卖盗版书和盗版光盘的,还有开录像厅放黄色录像的。目前青少年的性教育大多是自学成才,有人不惜节衣缩食去地摊上买本《新婚必读》,金西博士和海特博士的性学报告比砖头还厚,价格却相当便宜,这全是拜盗版书商所赐,他们无意间扮演着对青少年进行性启蒙的角色。这些博士们的作品大多是学术著作,文笔虽然流畅,但不能给人以文学上的享受,它们的作用就像馒头一样只能充饥,味道则差了点。(张竞生博士和李银河博士的性学作品则与众不同,文笔优美,读起来很不错的。)
古人曾说雪夜围炉读禁书是人生一大快事。在清朝,《金瓶梅》是禁书,可是文人兼政府官员纪晓岚先生就敢读,还当着众大臣的面以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为下联对句;《红楼梦》也曾是禁书,被政府和某些道德君子称为诲淫之书,文革大革命时它又受过此等礼遇,道德卫士们文网之密,古今无不同。
如今人们把那些性描写占一定比例的书称作黄书,打入毁禁之列。我们上中学时就读了不少黄书。现在想想,那些黄书写的其实是很拙劣的,情节简单,文笔平淡,有时候光描写呻吟浪叫就用了一页甚至好几页,一个啊字后面会整行整行地用省略号,这说明作者文学修养的低下。相比之下,作家们写的黄书就出彩多了,他们至少会用比喻,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。我上中学时还读过田雁宁等人的爱情小说,他们写性就比棉棉卫慧要有文采。